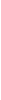君舍开始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清晨准时出现在这扇窗前。
运河的晨雾还浓得化不开,男人已经端着咖啡倚在窗边,那是他新一天的开幕仪式。
他看着她几点醒来,几点出门,又几点裹着一身消毒水味归来。
她走路总微微低着头,像在数地上的鹅卵石。一紧张,就会无意识咬嘴唇,把那点可怜的嫣红咬得发白。只有见到那个傻大个时,才会偶尔露出一点笑容,眼睛弯成月牙
她作息比巴黎时期更混乱,八点半雷打不动推门而出,却常常要待到街灯一盏盏亮起来,才肩背垮着,拖着疲惫的影子回来。
“准时又敬业的小兔。”他对着空气举杯,仿佛在致敬某种可笑的精神。
敬业到了….近乎自虐的地步。啧,就凭那副风一吹就倒的身子骨?君舍的眉头皱起,指节在窗框上叩出轻响来。不过,这点无名火来得突然,去得也快。
救世主情结泛滥的小兔,他嗤笑。
偶尔,她会拐进街角的面包店,买那种撒着糖霜的硬饼干。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像捧着什么珍宝,那大概是她在血污与死亡之间,给自己预留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慰藉。
而那条克莱恩留下的杜宾犬......
君舍的指尖在望远镜上收紧。那个刀疤脸尽责得令人叹为观止,几乎寸步不离,好几次,他的座驾滑过时,隔着布帘,他都能感到那道视线如刺刀般追随着,直到拐过弯道,才堪堪收回。
好狗,君舍唇角扯了扯,可惜跟错了主人。
他没有贸然接近,鼻梁似乎还记得华沙那一拳的钝痛,更难忘的,是倒地时后脑撞击地毯的闷响。那个死掉的波斯商人品味确实不俗,手工地毯软得能缓冲撞击,却缓冲不了他当时的狼狈。
公务闲暇的时候,他会顺便换个地方透口气,权当是熟悉阿姆斯特丹。
红十字会侧面的废弃仓库里,积灰的窗沿正对手术楼。他征用这里的理由冠冕堂皇:“监视可疑人员流动”。
此刻他正倚在窗边,指尖夹着刚破译的电文。指腹轻轻一弹,纸页发出轻响,眼底浮起一丝玩味笑意来。
“风车”的下线,这几天终于露头了。
叁处可疑信号源,每周叁下午准时出现,两个在运河区的古董钟表店阁楼,另一个在大学植物园的配电室里。锁定的人选也浮出水面,一位图书管理员,一个在港口清点香料桶的报关员,还有一个——
他的目光在第叁行档案上停留,艾歇巴赫空军少将的老管家。
说起这个,还真该好好谢谢小兔,她总是能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提供最绝妙的灵感,他漫不经心地想着。
前几天纯粹出于无聊,他翻看了占领区军官管家的备案资料。原本是想查查照顾小兔的那位管家太太底细——事实证明,她干净得像漂白过的亚麻布,却意外瞥见另一个名字:格蕾塔·施莱特。
附件里夹着1940年的推荐信复印件,落款是某位已故的西里西亚伯爵夫人,措辞华丽得像咏叹调,语法却露了马脚:一个格助词的用法,分明是柏林北部方言区的风格,而非西里西亚腔调。
他合上电文。“今天就到这里。” 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那个看不见的“风车”宣告今日休战。
该去欣赏下一幕了,他的阿姆斯特丹私人剧院特别场,每日准时开演。
两点左右,通常是人最困乏的时候。他总能看见她跟着那个傻大个儿穿过连廊,后者如古希腊石像般立在手术楼门口,守着她进,等着她出。
君舍靠在窗边,烟卷在指间静静燃烧,青白烟雾与仓库的霉味缠绵交织。
他闭上眼,轻易就能描摹出门另一边的画面。
她穿着洗手衣,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那双大得过分的黑眼睛,握着柳叶刀,穿梭于血肉之间时,是否找到了比祈祷更真实的救赎?
救人的滋味如何,小兔?他吐出口烟圈。
是不是比抄写那些早已凉透的名字,更能触摸到活着的实感?
—————
俞琬开始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像一缕不属于这个季节的阴风掠过皮肤去。
好像…总是被谁看着。
起初只是隐隐约约的,后颈偶尔发凉,走在连廊时总错觉身后有脚步声,可每次回过头,只有风穿过空荡荡的拱门。
她以为是太累了,白天面对源源不断的伤员,到了晚上,寂静的房间里是望不到头的担忧,神经绷得太紧,难免会疑神疑鬼。
可那感觉并没有消退。有时是在走廊拐角,有时在大宅窗前,甚至只是站在红十字会门口等雨停的时候….
那注视不像恶意,也绝非善意。它只是….存在。像房间里多了一个透明的幽灵,不靠近,不打扰,只是安静地停留在角落,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有时,她觉得那视线像博物馆玻璃后的参观者,礼貌地保持距离,却执着地丈量着每个细节。
她试过假装看书,用余光把窗外一寸寸扫回去,甚至试过在窗玻璃上涂肥皂水,听人说这样能反光,看见背后的东西。
但什么都没有。唯有运河对岸那栋灰扑扑的小楼,叁楼永远拉着墨绿色的窗帘,像几双阖上的眼睛,
是错觉吧,她对着茶杯里的倒影喃喃。连着做了一周手术,又睡不好,压力太大而已。
可那种感觉却像苔藓似的蔓延,越试图抹去,越是渗出凉冰冰的湿意。
早晨出门时,她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飘向对岸去,那儿有一排老房子,窗户大多都钉着木板,倒也有几扇开着的,她总觉得其中一扇后面,藏着眼睛。
可当真定睛看去,后面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更让她不安的是那辆黑色奔驰。
它不像其他军牌车那样招摇过市,每隔两叁天,在她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大门时,总会瞥见那辆车停在街角,白纱窗帘将车窗遮得密密实实的。
和巴黎那辆奇怪的轿车一模一样。
第一次看见时,她以为自己眼花了,巴黎的一切,早该留在巴黎了。第二次,她驻足凝视,车子却像有生命般缓缓滑入巷弄,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叁次,她故意放慢脚步,假装在欣赏河面上漂浮的梧桐叶。可那辆车总在她靠近前就离开,留下一缕淡淡的尾气,消散在暮霭里。
那天夜里她做了噩梦。
梦见自己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但所有的建筑都扭曲成了巴黎的轮廓。她拼命跑,石板路在脚下延伸开去。而那辆黑色奔驰就在身后,优雅得像一只散步的猫。
她转弯,它也转弯。她躲进小巷,它就停在巷口,引擎低低地哼着,耐心得像在等一只迟早会跑累了的兔子。
最后她跑到了运河边。水面黑沉沉的,没有月光,也没有驳船。无路可退。
车门开启,锃亮的黑皮鞋率先落地,紧接着是利落的西装裤线,最后是——君舍。他朝她微笑,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笑。
“小女士,”轻飘飘的嗓音从梦境深处浮起来,裹着薄荷烟的清凉。“玩够了吗?该回家了。”
女孩惊醒时,冷汗已然把睡衣浸透了。
窗外,阿姆斯特丹寂静极了。只有运河的水声,一下一下拍打着岸边,像某种不祥的低语。
真正的恐惧,在一个寻常的、她几乎说服了自己那只是噩梦后的冬日,猝然照进现实。
那天下午,女孩在手术室待得比平时久些。一个十八岁的士兵,弹片卡在肝包膜附近,稍有不慎就是大出血。维尔纳没说话,只看了她一眼,她便留下来配合。
等从手术楼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初冬的荷兰,白昼短得像被人偷走了一截似的。
约翰站在门边,就这么标枪似的立着,听到声响便倏地转过身来,黑暗里看不清表情,但她知道他在看表。
“对不起,”俞琬快步走上前,“那个伤员太危急了……”
“该回去了。”约翰打断她,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
俞琬咽下解释,安静地缩到他身后半步去。
她明白他在担心什么。天黑后的阿姆斯特丹并不安全。不只是盟军的轰炸机,还有那些对占领军恨入骨髓的眼睛,比空袭警报都更难防备些。
两人快步穿过院子,朝着主楼稀疏的灯火走,夜风卷起枯叶,打着旋滚过去。
就在这时,她的脚步顿住了。
那种熟悉的、如同小虫爬过后颈的异样感又上来了,她几乎本能地抬了抬头。
视线仓皇地扫过对面那排黑黢黢的仓库,维尔纳随口提过,那里从前是某个布料商的货栈,空置多年,玻璃窗大多被撬走了,只剩下一个个空洞洞的窗框。
但其中一扇,二楼的,是完整的。
不仅完整,还擦得太干净了,像一块漆黑的,微微反着光的镜子。而就在那块镜子中央,她仿佛看见了一个人影。
一个穿大衣的男人静静立在窗前。指间夹着猩红的光,该是香烟,那红光明灭闪烁,像一只眨动着的眼睛。
他在看着她,又或者说,是在绵长地瞧着她和约翰即将离开的方向。
距离太远了,天也黑,她辨不出面容来,但那轮廓,那副懒洋洋的站姿,那种仿佛置身丝绒包厢里,居高临下欣赏一场专属舞台剧的悠闲态度——
心脏停跳了整整一拍。
像他,像巴黎那些“偶遇”的午后,他嘴角噙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笑意:“小女士,又见面了”;也像他带着伊藤的尸检报告坐在面前,目光像游标卡尺般测量着她每一寸表情,让她从指尖凉到心底。
真的有人在看。
那是种被天敌锁定的感觉,像狐狸蛰伏在兔子洞之外。
“文医生?”约翰察觉到她的异常,身体本能侧过来,像一扇铁门挡在她和未知之间。
女孩僵硬地指过去:“那、那里……”她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在抖。“刚才有个人……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们。”
男人浑身立时绷紧了,他按住枪套,军人特有的警觉如冷刃般从眼底划过,迅速看向仓库二楼。
那里空无一人的,只有一块玻璃,映着铅灰色天空中最后几缕暗紫霞光。
风吹过院子,枯枝上的乌鸦嘎嘎叫了两声。
“什么样的人?”男人沉声问。
俞琬站在原地,怔怔地盯着那块玻璃。真的有人吗?还是我已经被那个噩梦追得太紧了,紧到连光影的作用,都能凭空勾勒出君舍的轮廓了?
“我……”她张了张嘴,半晌,脑袋又无力地垂下来。“也许是我看错了。”
她试图笑一下安慰自己,可嘴角刚扬起来,跌落回去。
但如果真是君舍呢,如果他真来荷兰了呢?这几乎称得上荒诞的认知,像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浸透四肢百骸去。
为什么,他又发现什么了?所以不惜千里迢迢来到这看着她?
这一刻,她发现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
这个周四的下午,君舍确实有公务在身。
红十字会隔壁街区的市政厅,叁间审讯室,六名公务员,准确说是六只吓破胆的荷兰鼹鼠。抵抗组织给他们钱,他们提供干净的身份证明和食品配给券。直白、老套、毫无想象力。
审讯过程乏善可陈。那些荷兰人要么涕泗横流地求饶,要么装傻充愣。君舍用了点“小手段”,并非肉体上的,他想开更喜欢心理压迫的艺术,很快就得到了想要的口供,哭着喊出来的。
无趣,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结束。
走出市政厅时,河风送来面包房的焦糖香气,甜腻得令人皱眉。
“回官邸吗,上校?”司机躬身拉开车门。
君舍看了眼手表,灰蒙蒙的天空压着皱巴巴的屋顶,也压着一排排营养不良的梧桐树,像幅没干透的水彩画。
这个点,她应该还在手术室里,握着那些寒酸的器械,从死神指甲缝里抠人。
而某个柏林来的闲人,站在街边,像一个没写进日程表的问号。
君舍搭着车门,一条腿踩着踏板,一条腿还稳稳落在石板路上。“不。”
他需要走走。审讯室里那股恐惧的酸臭味还沾在领口,需要风吹一吹。再说,阿姆斯特丹的运河确实比柏林施普雷河更上相。
他示意司机先走,“我自己回去。”
而后,男人沿着王子运河踱步。深灰大衣配烟灰围巾,棕发被风吹得凌乱。手里卷着的报纸让他像极了哪个大学的哲学教授——如果忽略眼底那抹过于锐利的冷光的话。
他确实在欣赏运河风光,顺便抽支烟,顺便...让目光自然而然地滑向那栋红白标志的建筑。
纯属职业习惯,就像每天早上刮脸时会端详镜中的自己,走进房间会先扫视潜在出口,没什么特殊含义。这只是他熟悉这座城市的必要程序。
接着,他看见大门被推开——
先出来的是那个傻大个,站在台阶上左右扫视,像台人形雷达。确认安全后,才朝门内点了点头。
几秒钟后,小兔蹦了出来。
浅紫色毛衣配黑呢大衣,衬得皮肤愈发瓷白。品味比克莱恩那套万年不变的军装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两人并肩走下台阶,可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坐进轿车,而是朝东边的街道走去。
君舍挑了挑眉,慢悠悠跟了上去。
距离保持在大约叁十米,中间隔着叁四个行人,还有一个骑自行车摇摇晃晃的老先生,既不会跟丢,也不会被察觉,这是狐狸的基本功。
他饶有兴味地看她走路的模样,脚步很轻,很快,像只赶在日落前回窝的小动物。偶尔会抬头看看天空,或者和杜宾犬说些什么。对方只是点头,偶尔从喉间挤出一个单音节。
真闷,君舍无声嗤笑,跟那种木头待一整天,她居然不会无聊到睡着。
走过两个街区,在人字形岔路口,她忽然停下来。女孩指着那条窄巷说了句什么,傻大个看了眼腕表,终于点头。接着,她便独自飘过马路。
风很大,但此刻俞琬的手心里全是汗。
她是去买香料的,肉桂,丁香,还有一小块姜,克莱恩在信里说阿纳姆一直下雨,她帮不上别的忙,只能配点暖身的茶寄过去,哪怕知道十有八九还是会寄不到。
香料店藏在老城区的窄巷深处,海伦太太带她去过一次,门面很小,罐子里装着五颜六色的粉末,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打喷嚏的辛辣芬芳。老板娘是个印度裔老妇人,战前就从孟买漂洋过海而来,口音浓得需要连蒙带猜,可笑容很温暖。
她定了定神,抬脚迈入窄巷。
这几天,那种感觉越来越具象了。早晨起身时,总觉得窗帘缝后有道人影闪过去,走在街上时,也总觉得某个橱窗的倒影里,有一双褐色眼睛在看着自己。
她需要一点证据,证明是自己想多了,或者……证明是真的。
巷子比记忆中更长,但并不危险,这是阿姆斯特丹最常见的老式窄街,两边都是砖砌的老房子,白天里也总有行人来来往往。
俞琬走得很慢,不是因为不赶时间——她在感觉。整个过程她都得竖着耳朵,滤过自己的脚步声、远处的汽笛、还有窗户后收音机的杂音。
她在辨认,身后有没有那种像猫一样从容的皮鞋声,有没有衣料的窸窣,甚至….裹着薄荷烟味儿的呼吸?
走到中段时,她忽然停下来。
那种感觉又来了。像有人用指尖点在她的脊椎上,不重,但存在感强得无法忽视。她甚至能想象出那双眼睛来,棕色的,像融化的蜂蜜,可深处却像结了一整个冬天的冰。
葡萄宝宝的长评:
琬想要提着手枪去找那些可能会影响德牧上校生命安全的人“清算”的冲动,应该是出于极度的惊惧和担忧后的暴怒,当理性被硝烟侵蚀,情感便以最原始的形状破土而出。她知道克莱恩在意她的生命超过自己,所以也想用自己超负荷工作、不好好吃饭来引起克莱恩的牵挂,琬本身很坚强,用这种刻意的弱化自己,也可以看出战争到了很焦灼的阶段。之前琬在风车里亲吻克莱恩的伤疤,那个时候她应该也会自责为什么克莱恩受伤的第一时间她不在现场为他包扎。或许正是这份后知后觉的疼痛,让她明白了:在战争的铁幕下,守护一个人最艰难的方式,不是替他挡下所有子弹,而是在破碎的间隙里,一遍遍确认彼此活着的温度——无论用愤怒,用伤口,还是不够温柔的誓词。
米妮宝宝的长评:
笑死了君舍现在的行为我总想象的是某狐拿着望远镜一边眼冒爱心一边对着小兔垂涎欲滴的咽口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而且君舍对待其他人哪怕是自己的上司都会讽刺挖苦两句,但是对琬的评价全都是很高很正面非常欣赏的,美的毫无防备啊,重新站起来继续握着手术刀用清澈的双眼注视着世界等等,哪怕有时候没忍住发神经,也会后悔然后开始自我检讨(即使会死鸭子嘴硬左右脑互搏)君舍这辈子所有的内耗基本都是和琬有关了hhh
半夜失眠的时候某狐belike:后悔!太后悔!当初没有给小兔留下一个好印象,怎么就憋不住这张有毒的死嘴呢(扶额
种菜宝的长评:
搜了下君舍看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才理解为什么他看这书,故事有点他们叁人的影子,只是他应该不会像维特那样轰轰烈烈的爱。君舍你要别老是在阴天阴暗或者晚上出现吓小兔,和偷偷摸摸的,小兔或许想你都像正常人。虽然君舍比小兔大很多,但君舍感觉还没小兔成熟呢。。小兔还是蛮了解君舍的,眼睛看起来像融化的蜂蜜,深处又像冬天的冰。
大大说到之后君舍也要解决就业问题,太期待他会选择做什么了,风骚的狐狸感觉做什么都风骚。君舍真的很享受有小兔在地方,他们以后会住一个城市吗?
太期待只有如果有的if线,他们的恋爱应该就是很好的玩的开展
本站所有小说均来源于会员自主上传,如侵犯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