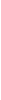第425章 死不旋踵
距离晋阳宫三个街区,保义军衙內控鹤都都將李重胤.,正眯著他那双狭长的眼睛,死死地盯著前方的血腥战场。
前方的街道之上,杀声震天,兵刃的碰撞声、临死的惨叫声、以及受伤战马的悲嘶声,衝击著所有人的理智。
这些本该用命边防的精锐武士们,就在这晋阳宫外的街道上杀成一团。
鲜血与断肢,早已將青石板铺就的路面,染成了一片暗红。
现在是这场巷战最为关键的时刻。
双方都已將自己手中能动用的兵力,尽数投入到了这片街区,且都在卯足最后的一口气,將对方彻底击溃。
看了片刻,李重胤的眉头就没有鬆开过。
不得不说,河东军真的是强藩,自己所部控鹤都是以草军河北帐的武士为军中骨干,剩下的纵然不是出自河北,也是草军中的悍勇武士。
但就在他这样猛攻中,自己这一边却是丝毫占不到什么便宜。
那些河东牙兵装备和自己相当,战技也嫻熟,而且是世世代代的武人出身,那体能是完胜这些草军悍卒。
要不是在斗志和韧性上差了点,他们控鹤都怕是要寸步不能前!
现在,他这边,除了留下一个营作为最后的预备队,其余的四个营,已经全部被他毫不犹豫地压了上去,没有丝毫的保留。
在刚刚抵达这片战场之后,他便立刻將自己手中一半兵力,压了上去。
而现在看到进展依旧缓慢,李重胤指著扈卫在旁的左营將王审权下令:“你立刻带著所部拿弓弩上两侧二楼,居高临下攒射那些敌军,为前面的王惲、王贤父子开路!”
王审权是魏博老兄弟,听到这话后,犹豫了下,还是说道:“都將,我要扈著你,我这边上去了,你身边再无人护持,太危险了!”
可他话刚说完,李重胤一鞭子抽在了王审权的兜鍪上,打得他满头金星。
然后就听李重胤怒骂:“王三,让你上就上!胆敢再有一句废话,我现在就废了你,免得你死在军法上,给我河北帐丟人!”
“我告诉你,算命的告诉我,我能长命百岁!这里是老子的建功地,不是埋骨所!给老子上!”
王审权再不敢多话,衝著所部怒吼:“娘的,咱们魏博人什么时候孬过!都跟老子冲!”
说完,王审权亲自带著一队人在前,一头撞进了街道左边的邸店里,和里面的河东牙兵杀做一团。
此刻,身边只有十余扈兵在侧,李重胤立在都旗下,一步没动。
他为何要拼?
那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很清楚,正是因为他们降將出身,所以更需要比那些老保义將付出干倍以上的努力。
既然上对了船,那就要拼到最后一口气!
现在,顶在最前面廝杀的是王惲、王贤父子带领的前营。
他们和李重霸兄弟一样,都是草军降將,不过他们並不是河北人,而是许州人。
他们父子都是许州本地的角牴士,因为在一场赌赛中失手打死了对面,使得对面背后的贵人输了大钱,这才背井离乡,后面隨其他绿林豪杰投奔了草军。
之后他们就隶属在了李重霸的摩下,做了善战步將。
从接战一开始,父子两人就带著二百披甲重步死死顶在街道上,血斗前进。
此时,街道上,到处都是嘶吼,每一个置身於此的人都在发疯,所有人都在肆虐著心中的兽性。
立於阵前的前营將王惲,披甲在身,雄壮的身体直接將甲冑顶起,浑身浴血。
——
他用手里的牌盾一下抽飞了一人,然后一斧头將对面的河东牙兵给砸死。
猛烈的力道一下子就將牙兵的甲冑给砍成了碎片。
但越来越多的牙兵冲了过来,王惲衝著前面的儿子大吼:“大郎,去!带著营里的突骑从侧面衝击!”
他的儿子王贤將铁骨朵朝天一竖,然后带著二十余突骑奔了出去。
身披著厚重的铁鎧,年轻勇锐的王贤,此刻正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衝杀在队伍的最前方。
他的手中,紧握著一柄沾满了血污的铁骨朵,每一次挥砸,都带起一蓬血花。
红的白的,全部都从铁锤尖顺著木柄往下流,滑得握都握不住。
在他身后百步的地方,他的父亲王惲,正带领著二百名重装步卒,结成密不透风的盾墙,一步一个血印,缓缓向前推进。
突然,从侧面的一条小巷之中,猛地衝出了一队约有百骑的河东左厢牙骑!
侧后有骑士惊恐大吼:“敌袭!”
有些个骑兵正拨转马头,试图迎击。
然而,已经迟了。
控鹤军的骑士几乎都已停止了衝击,所以面对这些骑著高头大马的河东骑士的迅猛衝击,几乎是在瞬间,便被冲得七零八落。
最外围的几个骑士仓促之间,连马头都没有调,就被后面衝来的河东牙兵们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將他们一个个地从马背上劈落。
倖存的控鹤军骑士们没有办法,只能夹著战马,向前溃奔,身后,那些河东牙兵们穷追不捨。
双方就在另一条街道上,一追一逃,一同冲向了街道的尽头,也就是去往衙署区的方向。
而就在此时,异变陡生!
当这些控鹤军衝出街道,来到一片空地时,只见广场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保义军突骑。
他们正是刚刚占领衙署,完成集结的二百飞龙突骑。
一看到自家骑兵袍泽被追,这些飞龙突骑只是將手里的角弓抬起,对著那些追兵攒射过去。
看到前方是袍泽,仅剩的十来个控鹤突骑连忙从左右两侧分开,將后面的河东骑士给露了出来。
战马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们在看到前方堵著一大群同类,几乎是出於本能地,便自发地减速、停止,任凭背上的主人如何抽打,都不愿再向前衝撞一步。
然后就靠著惯性,那些河东骑士撞在了飞龙骑的阵地里,人仰马翻。
短暂的混乱之后,便是更为血腥的近身搏杀。
“下马!结阵!”
一名飞龙骑的队將,声嘶力竭地大吼著,得令的骑士们纷纷翻身下马。
而对面,河东牙兵们也同样选择了下马步战,而且更为凶悍。
这些番汉混合的牙军骨子里就是残忍的,此刻嚎呼著,举著各种铁鞭、铁斧、铁骨朵和飞龙骑撞在了一起。
整个街口,彻底化作了一座绞肉机。
在袍泽们都被裹挟到了另一个街口后,王贤却因为躲避及时给绕开了。
抬眼间,他看到街口的酒肆二楼,出现了几名控鹤军。
这些人正要依託著窗欞,用手中的步弓,向下方拥挤的牙兵们拼命射箭。
但因为没有携带破甲箭,短小的箭矢很难穿透那些河东牙兵身上的厚实鎧甲,於是这些人正不断向下面的袍泽大吼:“箭轻,去换破甲箭来!”
“他娘的,快去啊!难道要等外面的兄弟们都死绝了?”
——
一阵阵脚步声,远远的,已经有甲士背著一捆捆破甲箭艰难地奔了过来。
这些破甲箭,一根的长度就顶得上普通箭矢的两倍,其中铁箭就占据了箭矢的三分之一长,用两石角弓射去,一箭就能穿破铁鎧。
街道下,那些河东牙將们还不当回事,有些牙兵身上都掛著十来支箭矢了,这会都和没事人一样。
可忽然看到对面的保义军正背著破甲箭往酒肆跑,直接嚇得声音都变了,飆道:“妈的,这些狗崽子换破甲箭了!快快快!弓弩手在哪里!”
“去杀了那些人,快啊!”
恐慌越来越大,一些河东军弓弩手也反应过来,被推著到了阵前,就对那些背著破甲箭的控鹤军射去。
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这些河东军身上,那就是他们的箭矢也同样破不了控鹤军。
他们就眼睁睁地看著,十来个甲士背著一捆捆破甲箭,衝进了酒肆里。
完了。
这些甲士一进酒肆,就全部累瘫在地。
其中一个甲士把身上的衣甲全扒了,对上头的袍泽大吼:“狗东西,赶紧来取箭!妈的,你们但凡浪费一个,老子就弄死你们!”
“跑死乃公了!”
酒肆二楼的控鹤军们哈哈大笑,相互將破甲箭传著,送上了二楼。
然后一名弓弩將残忍一笑,抽出半人高的破甲箭,猛拉弓弦,对著楼下街道的河东牙兵就是一箭。
只是一箭,此前还金身不破的铁鎧,瞬间就和纸糊的一样,直接被洞穿。
那河东牙兵整个人都定著了,然后握著半截破甲箭,缓缓倒地。
接著,越来越多的破甲箭矢,从酒肆二楼射出。
原先还结著阵的河东牙兵,顷刻间,就和麦子一样,成片成片的倒下。
军阵一下就崩了。
当控鹤军前营结阵平推过来时,已经慌不择路的河东牙军直接红著眼睛,调转刀头,向著身后的同袍胡乱砍杀。
而他们的身后还空著一批战马,此前这些人要守这处街口,就將战马放在了后面。
而当混乱传到了这边,战马也不可避免地被砍杀。
“噗嗤!”
刀锋斧芒,砍断了马筋,划开了马腹。
战马发出悽厉无比的悲嘶,鲜血与內臟,流了一地。
战马本就容易受惊,更不用说这些两脚兽还拿著刀斧砍它们。
霎那间,战马开始疯狂地挣扎、嘶鸣、人立而起,试图摆脱这片死亡之地。
马匹之间,互相牵扯著韁绳与挽具,挤压著,衝撞著。
一些马匹在混乱中倒地,隨即更多的马匹被绊倒,层层叠叠地压在一起。
甚至这些战马反过来又冲向了那些河东牙兵。
此前还红眼的牙兵们,瞬间就被战马给淹没,即便是身上披著铁鎧,也在暴风骤雨的马蹄下,被踩成了碎泥。
但危险並没有结束。
这些战马冲向了正带队前压的控鹤军前营。
此刻,王惲大吼,声嘶力竭地呼喊著:“后退!都向后退!”
但他的声音,很快便被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与马嘶声,彻底淹没。
几乎是下意识的,王惲摸到了腰间的小斧头,衝著那些奔来的战马怒吼一声,奋力向前掷去!
飞斧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正中前面的战马。
但这一击只是斧头的斧背砸中了战马,所以战马只是被砸得顿了一下,就更加狂躁地奔了过来。
然后狠狠地向著王惲撞了上来!
“砰!”
关键时刻,王惲向著侧面拼命一滚,然后像个葫芦一样滚到了右侧邸店旁。
他这边刚跳开,后面列阵的控鹤军步槊手纷纷抬起步槊,冲那些奔来的战马猛顶。
可巨大的衝击,以及把他们的阵型撕裂了一个口子,可也正是如此,中间的控鹤军纷纷被两旁的袍泽拖到了一边,让这些发狂的战马穿阵而过。
见到这一幕,王惲这才心有余悸地呼出一口气。
可就在他准备爬起时,他忽然看见距离自己两步的地方,同样躺著一个人。
那人穿著一身华丽的河东军衣,头上的兜鍪都不晓得被打到了哪里去了,可手中还依旧握著半截已经断裂的横刀!
敌军牙將!
这一刻,对方也发现了王惲。
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力气了,但几乎是一瞬间,两人都选择向对方扑去。
但王惲更快。
他用自己的肩膀,狠狠地撞在了那名牙兵的腰间!那人手里的半截横刀一下就飞了出去!
“砰!”
接著两人如同滚地葫芦一般,一同撞碎了旁边早已残坏的木门,滚进了漆黑的邸店內。
邸店里,桌椅倾倒,一片狼藉。
两人在地上,展开了最原始的肉搏。
王惲凭藉著衝撞的惯性,死死地压在对方身上,双手如同铁钳一般,卡向对方的脖子。
然而,那名河东牙將的战斗经验,显然比他更为丰富。
他猛地一挺腰,用头狠狠地顶开了王惲的下巴。
剧痛传来,王惲的眼前,一阵发黑。
那牙將趁机翻过身来,反將王贤压在身下,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了疯狂的杀意。
王惲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放弃了掐脖子,转而用手指,狼狠地抓向对方的脸,两根手指,如同铁鉤,死死地扣进了对方的眼眶之中!
“啊!”
那牙將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惨嚎。
剧痛之下,他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王惲的手。
王惲感觉自己的手掌,几乎要被咬穿。
他也发了狠,不顾一切地挣脱了对方的撕咬,顺手抓起了身边的兜鍪,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著那牙兵的头颅,狠狠地砸了下去!
“砰!砰!砰!”
一下,又一下。
兜鍪碎裂,鲜血与脑浆,迸溅得到处都是。
那名牙將的身体,抽搐了几下,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这一刻,王惲一下子就顺著墙滑倒在地,他定定地看著前面那具尸体,看著血肉模糊的面庞,杀人如麻的王惲忽然就呕了出来。
忽然,外头传来震天怒吼声:“万胜!”
“万胜!”
然后是尖锐的嗩吶声响彻整个街道。
再然后,王惲就看著邸店外,数不清的保义军和忠武军奔了过去。
王惲喉咙有点疼,忍不住往旁边吐了一下,发现有血。
正发愣,那边儿子王贤奔了过来,他是一间间邸店挨个找的。
一进来,就看见躺在墙角的父亲,以及躺在那的一个河东牙將。
王贤不理会这人,跑了过来,將他父亲拉起,喘著气喊道:“父亲,援军上来了!我军已经杀进晋阳宫了!”
一听这个,王惲猛地抓著儿子的手,吼道:“那还愣著干啥!带著队伍杀进去!”
王贤迟疑了下,意思是父亲你身体还坚持得住吗?
可王惲却和一头髮疯的牛一样,啪的一下扇在了儿子的脸上,然后又一把抓住儿子的头,骂道:“看著我的眼睛!”
“我们他妈的是降將出身!这个时候不拼,什么时候拼!”
“等那些老保义把河东兵都砍完了,你再拼?”
“你我父子都是死人堆里活下来的,怕的是死不死吗?怕的是没一个机会!我还指著你给我光宗耀祖呢!”
“我们王家多少代人就指著我们这一次!这一次拼了,我的孙子,你的孙子,公侯万代!”
说著,王惲怒吼道:“所以,大郎!今日咱们父子只要死不了,就给我拿刀衝过去!”
“祖先都在下面看著咱们!干!”
说著,他踏步上前,手掌是钻心的疼,但他还是拉著儿子,冲街道混乱的本兵大吼:“还有气没!有气就跟著咱冲!”
“我们打的头阵,能让別人给抢了!”
“万胜!”
说完,这个中年武人再一次冲向了前方晋阳宫!
>
本站所有小说均来源于会员自主上传,如侵犯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