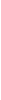第159章 隱世巫踪
杨灿从罗湄儿嘴里得到了满意的答覆,转身离去时,脚步都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刚刚出门,廊外的阳光还没照到脸上,杨灿便矍然惊醒:坏了,忘了我的纯情少年郎人设!
於是,身后的门將关未关之际,杨灿握起了右拳,用力地一挥,就差喊个“耶”字了。
然后,他又像生怕被罗湄儿看到似的,急急一回头。
果不其然,这孩子气的一幕,被罗湄儿看到了。
“果然啊——————,他是为了留我多住些日子。”罗湄儿被他那笨拙的雀跃,逗得唇角翘了起来。
想到杨灿为了留住自己,竟肯连天下闻所未闻的独家製糖秘法都拿出来分享,湄儿的心头便漾开了一圈小小的得意。
哪个女子心底没有藏著一个小公主呢?
那小公主总觉得自己就该是天下无双的,哪里容得別的女子分去对她的关注。
杨灿如今对她这般费心示好,那是不是说明,在他心里,自己正慢慢战胜那个女骗子?
想到这里,小公主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下巴微微扬起,眼角眉梢都染上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傲娇。
“哎哟,湄儿姑娘,你这换的什么素色衣裳?
先前那套粉綾袄子多衬你啊,穿起来活脱脱就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公主————”
卓婆子推开门走了进来,她是奉命来帮罗湄儿收拾行装的。
她就喜欢打扮罗湄儿,罗湄儿的底子多好啊,生就一副江南女子的好皮囊。
她的眼瞳澄亮得如同浸在溪水里的黑曜石,她的唇瓣是天然的粉润色,就像刚被春风吹绽的花瓣,她的肌肤白得就像是刚剥了壳的莲子,稍稍一掐都能渗出水来。
怎么可以打扮成这副样子呢?
简直是暴殄天物!
罗湄儿听得脸都黑了,她才不要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公主。
穿上那种粉嫩的衣服,整个人都软萌可爱得像个小女孩,太羞耻了!
她可是生长在武將世家啊!
卓婆子哪里知晓她的出身,在卓婆子眼里,这定是杨家將来的女主人之一,可不得提前巴结著?
她一边麻利地帮罗湄儿收拾著行装,一边用絮絮叨叨的抱怨,行夸奖讚美之事实。
罗湄儿被她照顾得无从插手,索性坐回椅上,思绪又飘回了方才杨灿的一番谈话。
去江南开一座双方合作的製糖坊?
这主意好像————好像真的很好!
赵家前些日子当眾拒婚,父亲嘴上说著“我儿值得更好的”,可他觉得很没面子,湄儿是知道的。
这桩婚事本是为了巩固两股政治势力联盟的一个纽带。
如今婚约告吹,不仅折了罗家的顏面,就连素来倚重父亲的大司马那里,恐怕也会有微词。
然而,我若是能带著製糖坊这桩稳赚不赔的生意回去,那可是一座看得见摸得著的“金山”。
哼,到时候,天下人都会说,赵家犬子安能配我罗家虎女!
如此一来,不仅能为我罗家挽回声望,更能帮父亲在大司马面前站稳脚跟。
想到这里,罗湄儿一双杏眼便慢慢弯成了月牙儿————
杨灿说服了罗湄儿,出来后就让卓婆子去帮她收拾行装,免得这小妮子心思多变,忽然又改了主意。
他得先把这小妞儿拐去上邦,然后琢磨一套縝密的合作方式、制定一套滴水不漏的契约,哄这小妞儿签字画押再说。
毕竟,那位罗大將军是什么人,靠不靠谱,他也不清楚。
可別一个不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隨后,杨灿便去了前堂,让豹子头盯著宅子里最后的归拢。
他和已然等候在此的李大目,去向阀主於醒龙辞行。
“公子,阀主已在花厅相候了。”老管家邓潯降阶相迎,笑吟吟地说。
李大目听了,不禁露出艷羡之色。
阀主在花厅召见,这可是不把杨灿当外人了啊,绝对是当成心腹在培养。
杨灿不卑不亢地点点头,隨著邓潯往花厅里走。
“杨灿,李大目。”於醒龙穿著常服,坐在花厅里,微笑道:“你们都已交接清楚了?”
二人齐齐施礼:“是,俱已交接清楚。”
於醒龙点点头,看向杨灿:“此去上邦,任一城之督,老夫对你期许甚深。
李凌霄老迈,上邦多有齟齬,你只管大刀阔斧,只要你踢得开局面,老夫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会全力支持你。”
李大目听了,羡慕地瞟了杨灿一眼。
杨灿微感意外,长揖道:“臣谢阀主知遇信重。”
於醒龙这一辈子都是优柔寡断的性子,前怕狼后怕虎的。
可他去年这一年来遭遇的重大变故太多了。
先是他精心培养多年的长子死了,而费尽心机新立起来的嗣子又太年幼。
接著他便被二房的於桓虎將了一军,虽然他暂时占了上风,可也和二脉彻底决裂了。
於桓虎发誓说从此要自禁於代来城,可不就是从此与他永不相见了么?
接著他最信任的外务执事何有真背叛了,而且是很早就背叛了。
如此种种,让於醒龙的心態彻底崩了。
他执掌於阀数十载,靠的便是步步为营的谨慎。
可去岁一年的连番惊变,恰似一柄重锤,生生砸碎了他固守的安稳。
长子殞命,二脉虎视,心腹背主————
这般锥心之痛,足以让任何沉稳之人,心境天翻地覆。
这老傢伙现在梭哈了!
他赌上了一切,要全力培养、扶持一批新人,逐步替代已经腐朽不堪的老团队。
唯有如此,等他儿子长大成人,才不会从他手中接过一个已经无可救药的烂摊子。
这人啊,一旦赌上了最后一笔筹码,倒是会变得光棍起来了。
於醒龙爽朗地一笑:“往日里老夫行事,总觉得既然一身系以全阀,自当谨慎小心,唯恐行差踏错!”
於醒龙坦率地道:“老夫错了,你年少锐进,心思活络,此去上邦,只管放手施为。
老夫,要看到新、看到变!”
这番许诺掷地有声,他竟也不避李大目。李大目是杨灿举荐的,那就必然与杨灿走的最近。
何况,他的打算,就算能隱藏一时,等他物色的年轻人纷纷走马上任时,也必然会被人知晓他的心意。
所以,於醒龙也就不遮不掩了。
杨灿长揖,沉声道:“阀主放心,杨灿此去上邽,必固城防、整吏治、安民心,求新、求变,绝不负阀主所託!”
於醒龙这才展顏,挥手道:“去吧,好生做事,老夫————等著看你,还我一个全新的上邽城。”
杨灿沉声道:“杨灿铭记此言,定不辱命。”
於醒龙转向邓潯道:“替老夫送送杨城督!”
杨灿行至凤凰山庄山门口时,大门两侧早已站满了送行的管事。
这些人里,既有长房的旧部,也有主院的管事们,一时间衣袍翻飞,人声鼎沸,极显热闹。
邓潯的到来尤其引人瞩目,他虽然只是主院的大管家,但他肩上却担著阀主的体面。
他这人一向不和於阀重臣私相交往,他能来,那就是代表著阀主。
这份分量,让凤凰山庄大门前的喧闹都淡了几分,眾管事不禁有些拘谨起来。
杨灿一一谢过眾人的心意,看著又一车沉甸甸的程仪被搬上队伍后方的马车,这才翻身上马。
在管事们的道別声中,杨灿一行队伍热热闹闹地驶离了山庄。
车厢內,赵楚生根本不顾车子的顛簸,依旧蹙著眉头思索,反覆回想师门旧人。
那些还有联繫,知道准確居所的,他都已经写好信了。
这时正在回想的,是那些已经失去联络,但还知道大致居住范围,如果派个送信人细细寻访,未必不能重新取得联繫的同门。
队伍行至山下鸡鹅山时,早已等候在此的旺財、胭脂、硃砂领著杨笑、杨禾等二十八子便兴奋地一拥而上。
队伍停下,上演了一出会师的戏码,瞬间让队伍的声势又壮了几分。
杨灿那粉雕玉琢的小女儿,趁此机会被青梅抱进了车厢:“这孩子还小,山风凉,可別著了风寒。”
至此,队伍里既有旧部亲信,又有新人,更混著妇孺婴孩,成分愈发复杂起来。
这般乱象之下,即便真有人对那婴儿的来歷起了疑心,想要追查根由,也只会陷入千头万绪的迷局,一时半会儿摸不到线索了。
待大队人马出了山区,前方道路上更有一支整齐的队伍等候在那里。
这是老辛给杨灿拉来的亲卫队,一共一百二十人。
这一百二十人,是老辛从八庄四牧里筛了又筛的好手。
他並非是按人头均分、从每处抽取十人的做法,而是实打实凭著本事论高低,挑出来的最顶尖的汉子。
如今的杨灿在八庄四牧威望正盛,更別提“去上邦城做城主亲信”本就是旁人求之不得的美事,谁不是拼著劲想入选?
老辛骑在马上,向杨灿一抱拳,大声道:“城督府亲卫,共计一百二十人!
他们个个能骑善射,拳脚功夫同样硬朗,皆是以一当十的好汉子,今向城督大人报到!”
在涇川与灵台交界的子午岭深处,千年古木如擎天之柱,枝椏交错间將日光滤得只剩星点碎金。
山壁被岁月啃噬出无数褶皱,那些天然溶洞便藏在这褶皱深处。
唯有寒冬时节,草木枯偃、叶落枝禿,这些隱蔽的洞口才肯露出些许轮廓。
西侧六盘山余脉的月亮山更是险峻,峰峦如刀削斧劈,陡峭得连常年攀山的猎人都要绕道而行。
这片山域名义上是慕容家的领地,可即便煊赫如慕容氏,也从无人敢深入腹地。
他们要取木材,只需在子午岭外围砍伐,那里的参天古木已足够支撑家族用度,何必去闯那连飞鸟都少至的险地。
没人知晓,那些幽深溶洞里竟有人烟,且绝非粗陋的避难所。
顺著天然形成的洞口往里走,不过数丈,眼前便骤然出现一道人工凿刻的石门。
石门厚重,推开时发出“吱呀”的沉响,门后是一处宽敞得惊人的洞穴。
洞壁上燃著的油灯昏黄摇曳,光线触不到洞穴的边际,仿佛这山腹里藏著一个未知的世界。
这是一处乾爽的旱洞,地面被反覆平整过,脚踩上去竟无半分碎石硌脚。
提灯人举著油灯前行,光影里能看见两侧依著岩壁隔出的屋舍,大多空无一人,也不知是做何用处。
约莫走了半里地,一根巨大的溶柱突兀地立在洞中央。
这溶柱形似倒生的古木,底端扎根於地面,顶端撑著三层楼高的洞顶,將溶洞生生劈出三条岔路。
向下深不见底,向前隱入黑暗,向右则透著一丝微弱的光亮。这溶洞群竟如迷宫般,藏著上下分层的玄机。
提灯人转向右侧,越往前走,光线越发明朗。
行至尽头,他忽然驻足,眼前的溶洞顶端裂著一道天然缺口。
天光如银练般倾泻而下,虽不及室外敞亮,却足够照亮洞底的景象。
缺口正下方,一汪温泉冒著裊裊白雾,氤氳水汽中,竟然生长著大片罕见的草药。
一两株或许是天赐野珍,可这般按品类分区、长势繁茂的规模,分明是人工精心栽培的。
围绕著温泉与岩壁,错落排布著数十间屋舍,往来人影穿梭。
他们行色匆匆,显然各司其职,见了提灯人便頷首致意,明显是认识的。
提灯人吹熄油灯掛在岩壁的铁鉤上,径直走向最靠里的一间石屋。
石屋从外看与其他屋舍並无二致,推开门却別有洞天。
外间屋里空旷无人,穿过一道雕花木门,暖意与光亮一同涌来。
数盏造型奇特的油灯从岩顶垂下,灯油燃得安静,將屋中央的单人床榻照得纤毫毕现。
床榻周围围著五六个人,有白髮垂肩的老者,也有面容刚毅的壮年人,男女皆有,神情却如出一辙的凝重。
提灯人放轻脚步凑上前,呼吸骤然一滯。
榻上躺著一个男子,约莫三十余岁,脸色青灰,裸露的肩头线条紧绷,显然已无生息。
最骇人的是,他的头颅被人用精密的细刃剖开了,脑部肌理在灯光下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怪哉,他的颅骨明明癒合得极好。”
白髮老者率先开口,指腹轻轻拂过创口边缘,语气里满是困惑。
“我们给他开颅清淤后,他的头疼之症明明已经根除了,这两个月饮食作息都如常,怎么会突然暴毙呢?”
周围几人立刻低声议论起来,一人甚至直接弯下腰,指尖触在死者脑部上方,细细观察著每一处肌理。
在这个视“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为铁律的时代,竟有这般开颅探脑的行径,简直是骇人听闻。
可鲜有人知,开颅之术並非无稽之谈,早在数千年之前它便已存在。
后世考古,曾发现一具新石器时期的头骨,骨上有一圈边缘光滑的规整孔洞。
那绝非打斗外伤,而是经过精心处理的手术痕跡。
从骨组织的癒合跡象推测,此人术后至少又存活了数月。
这个手术,想来是当时的医者为治疗他的头痛或癲癇所施的手段。
只可惜,这种古老的医术隨著文明演进,渐渐成了眾矢之的。
“伤体违伦”的斥责如潮水般將其淹没,被冠以“残体惑神”的罪名。
再后来儒家学说盛行,“身体髮肤不敢毁伤”的伦理观深入人心。
从此,这种侵入性的治疗手段,便彻底沦为“伤天害理的巫术”了。
它既背离了儒家伦理,又与阴阳调和、內服调理的主流医理相悖,执此术者自然也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巫邪之徒。
本以为此种巫术早就失传了,可是谁能想到,在这与世隔绝的子午岭深处,竟然还藏著这样一群坚守“异端之术”的传人。
白髮老者忽然抬眼,瞥见站在门口的提灯人,便对身旁眾人吩咐了一句:“你们仔细记录肌理变化,查找病变原因。”
隨后,他便向外间屋里走去,提灯人会意,默默跟了出去。
老者在墙角木盆中反覆洗了几遍手,抓著毛巾擦乾了手,回到原木的粗重大椅上坐下。
“什么事?”老者声音里透著难掩的疲惫。
他抓起桌上的陶杯灌了两口凉水,才缓过神来打量眼前人。
提灯人是个二十出头的瘦削青年,肩背挺得笔直。
他上前一步后,便压低了声音,语气既恭敬又凝重:“巫咸大人,慕容家传来消息,我们派往於阀的潘小晚,似乎有了异心。
產“巫咸”二字,本是上古时代一位著名巫师的名字。
传说那位大巫生於黄帝时代或者商王太戊时代。
此人通占星、精医道、善製盐,是当时朝堂倚重的一位重臣。
千百年后,这二字便成了巫家领袖的专属称谓。
没想到这伙剖开人头颅的怪人,竟然就是人人喊打的巫家传人。
而眼前这位白髮苍苍、精神矍鑠的老人,竟然就是巫家的当代掌门人,巫咸。
巫咸微微皱起眉,疑惑地道:“小晚,那孩子性子虽倔,却最懂我巫家处境,她————怎么会生了异心?”
提灯人道:“慕容家的人说,潘小晚对於慕容家派下的差使,常生懈怠敷衍之意。
慕容家派了一位木嬤嬤到她身边盯著,她也不为所动。
她非但不知收敛,还与木嬤嬤起了衝突,慕容家对她已极是不满。”
巫咸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抬手捏了捏眉心,一声悠长的嘆息在空荡的石屋里迴荡:“小晚这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
沉默在两人间蔓延了片刻,巫咸忽然抬眼,目光锐利如刀:“你该清楚,我们巫家,为世人所不容,一直被骂作妖巫、异端!
偌大的天下,都没有我等立足之地!
如今唯有慕容家肯收容我们,肯为我们提供安身之所,让我们继续钻研巫覡性命之学。
若是触怒了慕容家,我们又要重蹈先辈的覆辙,四处漂泊,居无定所。
巫家的千年传承,或许就要因此断送在我们手上。”
青年瞥见巫咸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气,顿时浑身一凛,深深低下头去。
“弟子明白。弟子即刻传信潘小晚,令她务必遵从慕容家的指令。若她仍然执迷不悟————”
提灯人顿了顿,咬牙道,“弟子会亲手把她抓回来,施以剥肤解骸极刑!”
巫咸缓缓頷首,目光重新投向洞外那片朦朧的天光,神色复杂难辨。
子午岭的寒冬还未过去,巫家的前路,似乎比这山腹更显幽暗。
本站所有小说均来源于会员自主上传,如侵犯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