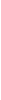就在京城那帮文官武將为了黑龙江的貂皮和台湾的硫磺抢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安平镇(原热兰遮城),年轻的郑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姓爷郑成功,正面对著他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烂摊子。
安平镇虽说是收復了,但那模样简直没法看。
城墙被明军的重炮轰得像狗啃过一样,到处都是碎砖烂瓦。街道上,荷兰人撤走前故意倾倒的垃圾发出一阵阵恶臭。最要命的是,这里的人心比这废墟还要乱。
“少爷,哦不,同知大人。”
一个老管家气喘吁吁地跑进那间临时充当知府衙门的破屋子,“出事了!城外赤嵌社那边,咱们福建刚来的移民和当地的高山社番打起来了!”
正在看地图的郑森猛地抬起头,那张还带著几分书卷气但已经初见稜角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
“为了什么?”
“为了水。”老管家擦著汗,“那几个移民要在赤嵌溪边开荒种甘蔗,把上游的水给截了。下游社番的村子没水浇田,就……就动起手来了。听说已经伤了好几个。”
郑森“啪”地一拍桌子,霍然起身。
他腰间掛著的那把佩剑是父亲郑芝龙给他的,剑鞘上还镶著宝石,看著贵气逼人。
“真是岂有此理!这些移民刚来就惹事?咱们是来安民的,不是来当强盗的!”
他抓起令箭,“点齐五十亲兵,跟我去看看!这帮刁民若是敢乱来,我先斩了带头的!”
这股子年轻气盛的劲头,像极了当年刚出海的郑芝龙。但不同的是,郑森读过书,是南京国子监的高材生,他心里有一套“王道乐土”的理想,容不得半点沙子。
刚衝出衙门,迎面就撞上了一个铁塔般的汉子。
那是施琅。
施琅穿著一身半旧的鸳鸯战袄,手里拎著一壶酒,看来是刚巡视完炮台回来。
“哟,大公子这是要去哪啊?杀气腾腾的。”施琅似笑非笑地拦住了他的路。虽然郑森是同知,但在军中,大家还是习惯叫他大公子。而施琅这个总兵,对这位含著金汤匙出生的少爷,向来是有点“看孩子”的心態。
“施將军。”郑森拱了拱手,虽然急,但礼数不乱,“城外移民与社番械斗,我去弹压。”
“弹压?”施琅嘬了一口酒,“你怎么弹压?谁有理帮谁?还是各打五十大板?”
“当然是秉公执法!谁先动手打谁!”郑森理直气壮。
施琅笑了,那笑容里带著一股老兵油子的狡黠。
“大公子,你读书读多了。在这地方,公理那玩意儿,有时候不如一壶酒好使。”
他用那只满是老茧的大手拍了拍郑森的肩膀,“走,我也去看看。不过你听我的,先把亲兵散了。带这么多人去,本来是抢水,別最后弄成了咱们官府去抢劫。”
两人骑马赶到赤嵌溪边的时候,场面確实已经快失控了。
一边是一百多號福建移民,手里拿著锄头、扁担,甚至还有几把藏著的腰刀。他们大多是刚从泉州漳州招募来的流民,穷怕了,见到地就想占,那股子狠劲不输海盗。
另一边是两三百名高山社番,赤著上身,脸上涂著红黑相间的图腾,手里拿著削尖的竹枪和弓箭,嘴里吼著郑森听不懂的土语,情绪极其激动。
中间已经躺了几个人,头破血流地在那哼哼。
“住手!”
郑森策马上前,一声断喝。他还真有点气场,两边的人被这一嗓子震得稍微停了一下。
“我是台湾府同知郑森!谁是带头的,出来!”
移民那边走出一个光膀子的壮汉,脸上还有道新添的血口子。他见是个年轻官员,也不怎么怕,拱手道:“大人,咱们是皇上招来垦荒的。这地给了咱们,水自然就是咱们的。这就帮生番不讲理,非要断咱们的財路。”
社番那边也走出一个头插羽毛的老者,虽然听不太懂汉话,但指著那条快断流的溪水,愤怒地比划著名。
郑森跳下马,眉头紧锁。
从法理上讲,移民確实有垦荒令。但从情理上讲,你把人家祖祖辈辈用的水给断了,人家不拼命才怪。
“这水……”郑森刚想说什么“平分”之类的话。
施琅突然跳下来,一脚踹在那个壮汉的屁股上。
“谁他娘的让你把坝筑那么高的?”
施琅骂骂咧咧地走过去,也不管那壮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直接走到溪水中间那个刚堆起来的土坝前,抡起手里的大刀,“哐哐”几下,把土坝削开一个大口子。
哗啦啦!
水流瞬间冲了下去,流向了社番那边的田地。
原本愤怒的社番们愣住了。
那边的移民不干了,壮汉嚷嚷道:“施总兵,您这是帮外人啊!咱们可是给您家郑大帅交过租子的!”
“闭嘴!”施琅回头就是一个冷眼,那眼神里带著杀过人的寒气,“老子帮的是理!这地是让你种甘蔗,没让你种成水田!甘蔗这玩意儿,耐旱,用得著把水截断吗?你就是想多占点便宜,顺便把下游那块地也想讹过来是不是?”
被戳穿心思的壮汉缩了缩脖子,不敢吭声了。
施琅这才转身面向那个社番老者。
他竟然从怀里掏出一包盐,直接扔了过去。
老者接住,闻了闻,脸上的警惕色消退了不少。盐,在这里可是硬通货。
“告诉他们。”施琅指著身边的通译(一个懂土语的老兵),“以后这水,三七开。你们七,他们三。但是,你们那边那片林子,得让我们去砍点木头修船。行不行?”
通译翻译过去。
老者和身后的社番商量了一会儿,点了点头,甚至还对著施琅行了个摸头的礼。
一场眼看就要流血的衝突,就这么被施琅几脚加一包盐给化解了。
郑森站在一旁,看著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他发现自己刚才想的那些“大明律例”、“教化万民”,在这片蛮荒之地,似乎真的不如施琅这“一脚踹”来得有效。
回城的路上,郑森一直沉默。
施琅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酒壶递过去,“喝一口?压压惊。”
郑森没接,但他问了一个问题:“施將军,若是以后移民越来越多,这种事天天发生怎么办?总不能每次都靠您去踹吧?”
施琅笑了,“这就得靠你了,大公子。”
他指著路边那些正在劳作的百姓,“我施琅是大老粗,只会杀人,顶多会这种和稀泥的手段。但要想让这地界长治久安,光靠这不行。你得想个法子,让这两拨人觉得自己是一家人。”
“一家人?”郑森喃喃自语。
他突然想起了父亲郑芝龙以前说过的一句话:生意就是把別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最好的办法不是抢,是让他觉得给你钱他也能赚。
郑森眼睛亮了。
“停车!”
他突然勒住马,看著路边一个卖鹿皮的社番少年。那少年正拿著一张皮子跟移民换几个铜板,眼神里全是渴望,渴望那移民手里的一把铁铁斧头。
“施將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郑森那张书生气十足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属於政客的光芒。
“您说得对,光靠法不行。得靠利。”
“我要在赤嵌城外开互市!”郑森的声音越来越坚定,“专门设一个鹿皮换盐铁的衙门。官府定价,不许欺诈。社番拿鹿皮来,咱们给盐,给铁锅,甚至给农具。但有个条件——他们得学种甘蔗,种出来的甘蔗,官府保护价收购!”
施琅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这能行?”
“肯定行!”郑森越说越兴奋,“还有,鼓励通婚在!告诉那些光棍移民,谁要是能娶个社番女子回家,或者把自家闺女嫁过去,官府免他三年的丁税!还要给嫁妆!”
这就是最原始的“经济统战”。当两拨人睡觉都在一个被窝里,吃饭都在一个锅里的时候,谁还会为了那点溪水拼命?
施琅看著这个眼睛发亮的年轻人,心里暗暗吃惊。
他好像在郑森身上,看到了郑芝龙当年那种算计天下的影子,但又多了一层郑芝龙没有的东西——那是读过书、见过大世面的人才有的格局。
“大公子。”施琅难得正经地叫了一声,“你这招,比我那一脚可是高明多了。这叫……在刀把子上掛糖葫芦?”
“不。”郑森摇摇头,眺望著远处安平港的海面,那里正停著大明的舰队,“这叫王道。只不过,是手里握著刀的王道。”
那天晚上,安平镇的同知衙门灯火通明。
郑森连夜写了一份《治台疏》,里面没有那些文縐縐的废话,全是实打实的利益算计:怎么收税,怎么分地,怎么用经济手段同化土著。
这封奏疏送到京城的时候,朱由检看完了,只批了四个字:“后生可畏。”
而这仅仅是郑成功(郑森)在这片海岛上的第一课。
他很快就会发现,治理这片土地,远比他想像的要复杂。
因为这海里除了鱼,还藏著比鯊鱼更凶猛的敌人——那些不甘心失败的海盗残余,以及正在暗处磨刀霍霍、准备反扑的荷兰联合舰队。
但至少现在,这颗未来的將星,终於找到了他的落脚点。
本站所有小说均来源于会员自主上传,如侵犯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