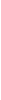热兰遮城的坚固,像是一盆冰水,浇灭了郑家军初来乍到的那股躁火。
“啃不动。”
这是郑芝龙盯著舆图看了半个时辰后,给出的唯一评价。
正面强攻,那是用人命去填荷兰人的火药桶,郑家虽然人多,但还没富裕到能这么霍霍的份上。尤其是那王承胤把“棱堡”吹得比阎王殿还邪乎之后,老海盗心里那点想一口吃个胖子的念头也就彻底断了。
“都督,若要下赤嵌,必走北线。”
郑森站在一旁,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道弧线,停在了台江內海的入口处。
那里有一个听起来很温顺的名字——鹿耳门。
“鹿耳门?”
郑芝龙皱起眉头,手里习惯性地盘著两颗铁胆,“那地方我知道。荷兰人在那里设了卡,但这不是要命的。要命的是水浅。那下面全是暗沙和铁板沙,大船稍微吃水深一点,进去就得搁浅。搁浅了就是红毛鬼的活靶子。”
他抬头看著儿子,“你想让弟兄们游过去?”
“不用游。”郑森摇摇头,转身招手,“把何斌叫进来。”
何斌是郑家在台湾的“內线”,原本给荷兰人当过通事(翻译),对大员的一草一木比荷兰人还熟。
这个身材精瘦、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一进舱门,就跪下磕了个头。
“大公子,小的算准了。”
何斌也不废话,从怀里掏出一本发黄的老黄历,“这是当地老渔民的看家本事。这鹿耳门水道,平时確实水浅,大船进不得。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大潮日,只要赶上那天时地利,水势能暴涨一丈有余!”
他伸出一根手指,眼神灼灼,“就在今晚子时。那是老天爷给咱们开的一道门缝。”
郑芝龙手里的铁胆停住了。
“一丈?”
“只多不少。”何斌篤定。
“好!”郑芝龙猛地一拍大腿,“若是真能过大船,咱们就能绕过热兰遮城的正面炮火,直接捅到赤嵌城的眼皮子底下!到时候,咱们的船就是移动的炮台!”
但他隨即又眯起眼,眼神变得阴鷙,“若是你算错了,几百艘船搁在沙滩上,本督就把你当沙袋填在海里。”
何斌把头重重磕在甲板上:“小的若有一句虚言,不用都督动手,自己跳海餵鱼!”
……
子时將近。
台江外海一片死寂。
为了隱蔽,所有战船都熄了灯火,帆也降下来一半。黑漆漆的海面上,只有浪花拍打船帮的单调声响。
郑芝龙站在“海龙王”號的船头,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
他身后,是几百艘满载士兵和火炮的各式战船。其中光是千料以上的大船就有几十艘。这是一场豪赌。如果今晚没潮水,或者潮水不够大,明日天一亮,这支搁浅的舰队就会变成荷兰人练习打靶的死物。
“水涨了吗?”他压低嗓门问。
一直在船舷边测水深的亲兵拉起绳子,借著微弱的星光看了一眼標记,声音有些颤抖:“涨了!都督!半个时辰,涨了三尺!”
郑芝龙没出声,死死盯著前方那片看不清深浅的水道入口。
又过了两刻钟。
“涨了五尺!”
“七尺!”
“一丈了!都督!真是一丈!”亲兵激动得差点把侧绳扔海里。
真的涨了!
巨大的海潮像是收到了龙王的號令,无声无息地涌入这条狭窄的水道,將那些平时露出狰狞面目的暗礁和沙洲一寸寸吞没。
“传令!”郑芝龙拔剑出鞘,直指正北,“全军入港!不得喧譁!违者斩!”
数百艘巨舰,像是黑夜中的幽灵,借著潮水的托举,悄无声息地滑进了鹿耳门。
船底下,原本会把船底刨烂的礁石此刻都在几尺深的水下沉睡。
但这並意味著绝对安全。
“水雷!左前方!”
冲在最前面的先锋船“定海”號上,突然传来一声惊恐的叫喊。
还没等眾人反应过来,“轰”的一声巨响,打破了深夜的寧静。
一团橘红色的火球在水道中央腾空而起,將漆黑的海面照得亮如白昼。
那是荷兰人不知从哪学来的阴招——“没良心水桶”。其实就是用大木桶装满火药,连著引线和机关,漂在必经之路上。船只要撞断绊索,立马开花。
“定海”號是艘先锋快船,这一下直接被炸断了龙骨,船头高高翘起,船上的几十名水兵像饺子一样被拋进水里。
“该死!”
郑芝龙骂了一句,“红毛鬼防著这一手呢!”
虽然只有几颗,但在这么窄的水道里,一颗雷就能堵住路。如果不能迅速清除,后面的大部队全得被堵在这儿。
“谁去排雷?”郑芝龙吼道。
这不是一般的活儿。水下黑灯瞎火,根本看不清哪有雷,哪有线,这基本上就是去送死。
“我去!”
一个精瘦的汉子从旁边的护卫船上跳了过来。
是陈豹。
他一边脱著身上的皮甲,一边骂骂咧咧:“妈的,老子在没当兵前,就是在水里摸珠子的。这点小阵仗还能嚇住老子?”
“算我一个!”
“还有我!”
片刻间,几十个平时在水里泡大的福建汉子站了出来。他们多是渔民、疍户出身,在水里比在岸上还灵活。
没有豪言壮语。
陈豹叼著一把短匕首,只穿了一条犊鼻褌,第一个跳进了刺骨的海水里。
其他人紧隨其后,像一群入水的水獭,瞬间消失在波涛中。
郑芝龙死死抓著船栏。
他知这帮兄弟是在拿命给后面的人铺路。
水下。
陈豹睁大了眼睛。
海水咸涩,刺得眼睛生疼。借著船头的火光,他隱约看到前方有一根根像蛛丝一样的黑线,连接著一个个隨著波浪起伏的大木桶。
那就是雷。
他憋住一口气,像条游鱼一样潜了过去。
这玩意儿结构不复杂,关键是那根绊索。
他游到一根索前,稳住身形,手中匕首轻轻一划。
线断了。
木桶失去了控制,顺著潮水漂向了一边。
成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这边刚切断一根,不远处就是“轰”的一声闷响。
一个兄弟可能太急,或者是水流太急没剎住,一头撞上了机关。水下爆起一团血雾,那人连个整尸首都没留下。
陈豹的心猛地一抽,但他不敢停。
他浮出水面换了口气,正好看到不远处的岸边,几个哨塔亮起了火把。
荷兰人的哨兵发现了!
砰!砰!砰!
岸上的红毛鬼开始用火枪朝水里乱射。
铅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朵朵致命的水花。
“快!別让他点了火!”
陈豹看到一个木桶似乎连著岸上的引线,他猛吸一口气,再次一头扎进水里。
这次不是切线。
他直接抱住了那个沉重的火药桶,用尽全身力气往旁边拖。铅弹在他身边嗖嗖穿过,有一发甚至擦破了他的肩膀,但他感觉不到疼。
他只有一个念头:把这拦路虎挪开!
“杀过去!”
船上的郑森看得目眥欲裂。
他拔出“延平”剑,指著岸边的哨塔:“火枪手!给我压制住他们!別让人白死!”
大船上的火枪手和弓箭手开始还击。密集的弹雨扫向岸边,把那几个露头的荷兰哨兵压得抬不起头来。
一刻钟。
仅仅是一刻钟,对於岸上观战的人来说,却像是过了一年。
海面上渐渐安静下来。
几具尸体漂了起来,隨著潮水晃荡。
“通了!”
水面上钻出一个脑袋,陈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和血,举起已经被砍卷了刃的匕首,嘶哑著嗓子吼道,“都督!没雷了!过!”
“过——!”
郑芝龙一声长啸。
庞大的舰队,再次启动。
那些几十丈长的大船,如同一条条甦醒的巨龙,碾过同袍用鲜血铺开的坦途,衝进了台江內海宽阔的胸膛。
岸边的荷兰哨兵绝望地看著这一幕。
他们最后的防线——那些看似无法逾越的暗礁和水雷,在东方人的智慧和血性面前,就像纸一样脆弱。
……
天蒙蒙亮。
热兰遮城。
揆一总督还没睡醒,都还在梦里盘算著只要守住几天,明军就会因为缺水而退兵。
“轰!”
一声巨响,连总督府的地板都震了三震。
不是攻城炮。
那是登陆的信號炮。
“怎么回事?!”揆一披著睡袍衝进作战室。
贝德尔上校像个幽灵一样站在窗前,脸色惨白如纸,指著北面的海湾。
“上帝啊……他们进来了……”
揆一衝过去。
在那片理论上“大船无法通行”的鹿耳门水道內,在那片平静的台江內海里,数百艘掛著日月旗的战舰,正如列队的骑士,整整齐齐地铺开了阵势。
而在距离赤嵌城不到三里的禾寮港泥滩上,无数的小船像白蚁一样涌向岸边。
成千上万身穿红色战袄的士兵,正扛著藤牌,抬著火炮,涉水登岸。
“疯了……他们疯了……”
揆一喃喃自语,“这不科学……昨晚並没有看见他们有大规模的行动……”
“是潮水,长官。”
一个老成的文官在一旁低声嘆息,“今天是东方人的初一。他们算准了潮汐。”
揆一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他引以为傲的天险,没了。
明军已经绕过了热兰遮城正面的火力网,直接把刀尖顶在了赤嵌城的嗓子眼上。
一旦赤嵌城失守,热兰遮城就会变成一座彻底的孤岛。
大势已去。这四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他的心口。
禾寮港滩头。
郑森第一个跳下齐腰深的海水。
他不想等亲兵来背。脚踏实地地踩在这片泥泞的土地上,踩在台湾岛的土地上,那种感觉才真实。
“告诉弟兄们。”
他回头看著正在源源不断上岸的军队,声音不大,却透著一股令人胆寒的冷静。
“上岸第一件事,不用埋锅造饭。”
他指著远处赤嵌城那条通往城外的唯一河流。
“去把那条河给我截断了。”
“没有水,我看这帮红毛鬼,是喝尿,还是喝西北风。”
风起了。
带著海水的腥咸和硝烟的味道。
一面崭新的大明龙旗,被郑森用力插在了禾寮港的最高处。
晨光下,那金色的龙纹仿佛活了过来,正对著不远处惊慌失措的赤嵌城,发出了无声的咆哮。
这是收復之战的第一缕曙光,也是西方殖民者在东方噩梦的开始。
本站所有小说均来源于会员自主上传,如侵犯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删除。